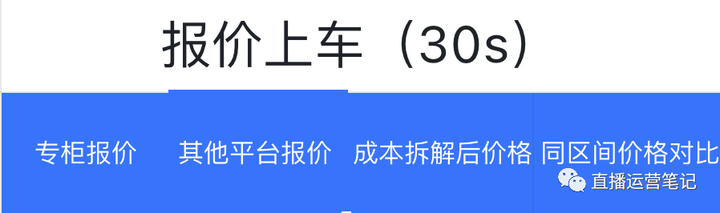前几天,我写了一篇《记文革初期我》的文章,对于文革初的我也只写了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红卫兵的,没有涉及半点派性问题,因为那个时期还没有分成派,写的确是亲身经历,完全是符合实际的,没必要去瞎编乱造。
可有个別的人,也许是因常给别人泼脏水习惯了,他自然进行胡乱地瞎喷,实在没喷的理由就用文章里偶尔岀现了个别错字,进大做文章,他以为伤害得了我,很不好意思,我大度,从不与小人计较,早已对喷子是不屑一顾了。个别错字也毫不影响我文章所表达的意思,别人能看得懂我文章的思想观点及立场,这就够了。
我是高二在校学生,在那个环境中,每个同学都参加了适合自观点的红卫兵组织,有些纯属是跟潮流跟某个人而参加,并认为参加红卫兵是件非常荣幸的事。既然是学生,必须服从学校的指令,还能有它选择的余地吗?在当时参加运动就如同是上课,难道你不去积极参加?对于我们平时都表现好的学生,更是应该积极响应而无二话了。
在当时的氛围,可以说没有谁他不参加的,连家庭岀身成份不好的同学,开始想参加表现一下自己还不大可能。自从红卫兵组织内部分裂为两大派以后,由于保组的血统论影响是不接受他们参加,后来也只好参加从原来红卫兵组织分裂出来的新生造反派组织,表示他们也积极在参加运动,也不会让别人瞧不起,却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后来的气氛与结局,认为就这样搞一下就完事,继续上课考大学。
文化大革命的总趋势是文的开始武的结束,正因为在造反中容纳了一些地富反坏子女,有一些以前在反右扩大化中被内定为右派但无结论的教师,还有一些在四清运动受冤枉为四不清干部,他们有冤无处申,也只有用造反来洗清冤屈,他们都是小心翼翼地参加到造反派外围的组织之中。
![图片[1]-记文革初期我-博云求真](https://picx.zhimg.com/80/v2-03f0352b8beac3b0b6f3297d51be6672_720w.jpg)
这些作为当时的政治环境,自然就成了紅色保派的把炳,认为造派队伍不纯,按照首都红卫兵初期血统论“只准红五类造反,不许黑五类翻天”,造派组织在有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成了翻天派,反革命组织,为后来的不测埋下了伏笔,比如被地方错误地镇反打成反革命,保组织头头扇动大批农民配合进城围剿,抓所谓的反革命份子,双方站据点使武斗的不断升级。
我们万县地区的文革在全国都算表现得上不但十分特殊而复杂,并且还残酷,这些自由研究历史的人來评判那段历史,我不好细说,也只作介绍不做评论。我只说我自己,文革初期参加了红卫兵,后又卷入了造反派,曾参加了大辩论,特别是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,批判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谬论。
因出头露面,被保组视为造反派积极分子,在那段称为红色恐怖的一个多月日子,年青十八岁的我,没遭到学校任何指责不什么是,却遭到一些农村不明真相的农民梱绑,消毒,批斗,但没有事实依据,只凭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,他们也没有我怎么样。
要说,文革中除了参加过写大字报大辩论,躲过武斗,没有參加武斗,但我在文革中同样是受害者,因为我也同样挨过捆,挨过斗,但我对那些整过我的人,文革武斗结束后,我懂政策并有一颗善良的心,我没有报复过任何一个人,相反他们因搞武斗失败外逃,被外地来支援万县的民兵抓获,从危难中我们把他们担保出来,口头说是交本地处理,实际上是还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,他们对我的以德报怨之举是万万没想到的。
![图片[2]-记文革初期我-博云求真](https://pica.zhimg.com/80/v2-5bd883c78cde41f81faef062436c8211_720w.jpg)
我们公社有点持殊,曾斗批公社书记的不是造派,反到是保派,迫害地富反坏右的也是他们,进城围剿所谓反革命的还是他们。我等却当上了救过公社书记的好人,因此,后来各个清查运动,我和几个战友都清白,没受任何影响,文革三年后却被公社领导们一致优先推荐,走出农村参加工作。
回想出来工作的几个同学,现都已光荣退休,还健在,比我的养老金还高许多。他们有的曾当校长就是我,有的干过县级法院副院长,交通局长,公社书记,公社武装部长,县级人大副主任,还有曾在珍宝岛参战转业后分到地委机关任党委书记的等等,都是曾参加过紅卫兵造字号的一些学生。
又回看在运动中,在我们公社曾假称也是造反派的农村骨干份子们,本来公社书是个大好人,非常艰苦朴素没什么问题,他们却没有事实根据地硬要狠批公社书记及干部,不留余地,后来三结合书记还是书记。十分积极的保组织骨干,当年跳得再高,一个也没调出去,农民还是农民,因做了伤天害理之事,基本上死得光光,基本上是因癌症而死。
报应,一切都是报应,在文革中无论哪派,有不怀好意的坏人,也有执行政策讲良心的好人,因此,我们对参加文革两大派,无论哪派都不能一概而论,不能以个人恩怨出发认定哪派都全是坏人,哪一派全都人好人,这样的作结论未免太绝对化了。